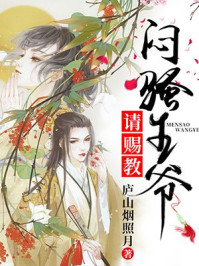如果展小白不是這麼在乎沈嶽,她可能會告訴他,她要長尾巴了。
偏偏,她是這樣的在乎他。
無論她怎麼努力,多麼刻意去想他的各種壞,都無法阻斷那種感覺。
磁場。
也許沈嶽說的很對,他們倆人之間,存在一個無法解釋的磁場,牢牢把兩個人的心拴在一起,永世不分離。
老百姓總說,丈夫往往是最後一個知道老婆給他戴帽子的人。
套用這句話來形容展小白要長尾巴的事,沈嶽絕對隻能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感受到溫熱的淚水,滴落在*上後,沈嶽輕撫着展小白嫩滑的後背,再次柔聲問:“究竟,怎麼了?”
“我要、我不能說。”
“為什麼?”
“不為什麼。”
“那,什麼時候才能告訴我?”
“等我,快要死時。”
展小白反手用力擦了擦淚水,嬌軀後仰,雙手扶着沈嶽的*,看着他的眼睛,輕聲說:“或者,你快要死時。”
沈嶽感覺,她肥皂劇看多了。
要不然,怎麼會說出這麼無聊的話來。
“沈嶽,别再問了。問,我也不會說的。來吧,我給你。但,你要小心呵護我。”
展小白按着他的*,緩緩起身。
沈嶽托住了她的雪、臀,阻止她坐下,搖頭:“這種事,需要情調。”
“好像你們男人不用情調的。”
“那我就不要。”
“那我就去嫁給慕容長安。”
“你敢。”
“我有什麼不敢的?”
“你究竟怎麼了?”
“你還沒死,我也沒死,現在不能說。”
展小白看出沈嶽沒那種意思,心中又在哭泣,表面上卻沒事人那樣,站起來:“你走吧。我現在也想開了,不會再管你和誰來往。更何況,就算是管,能管得了?”
“你特麼究竟怎麼了!”
沈嶽無比煩躁,随手扯過了衣服。
展小白隻是看了他一眼,撿起衣服疊好,放在床尾後,又從衣櫃内拿出一件白色睡袍。
沈嶽爬起來,飛快的穿好衣服:“我數三個數。你不說,我就走。走了後,再也不回來。”
展小白慢條斯理的攏着秀發,就像沒聽到他說什麼。
很快,沈嶽讀完了三個數。
展小白也半躺在了床頭上,随手拿過枕頭邊的一本雜志,翻閱起來。
砰的一聲,沈嶽大力關上了房門。
展小白卻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嘴角噙着淡淡的笑。
接着,門又開了,沈嶽滿臉不高興的問:“最後問一次,你究竟怎麼了。”
展小白想了想,才說:“我太愛你了。”
沈嶽問,她為什麼心懷滿滿的孤獨,無助和恐懼。
她說,是因為她太愛他了。
這算什麼狗屁答案?
沈嶽冷笑一聲,再次重重關上了房門。
等客廳房門也傳來砰地一聲後,展小白呆愣半晌,才伸手關上台燈,喃喃的說:“我太愛你了,這答案有錯嗎?”
愛一個人,很難。
不,是很疼。
展小白的尾骨蓦然痛過後,很快就沒事了。
現在,她又可以随便走路,坐着,滿地的打滾,或者和她太愛的人,做各種最劇烈的動作。
隻是,這痛來的太巧了些。
她在熄燈躺下後,有些發顫的右手,緩緩放在了尾骨處。
那兒,明顯比昨晚她臨睡覺之前,大了很多。
“我該怎麼辦?”
展小白默默問出這個問題時,任明明也在自問。
一整天的勞累,并沒有消磨掉任總對某種事情的渴望。
她實在搞不懂,她究竟是怎麼了。
她用她最出色的部位,給沈嶽提供無比的享受,嚴格說起來隻是一種交易。
她給他享受,他給她保護。
既然是交易,那就該和感情沒關系。
更談不上迷戀那種感覺。
可事實上,任明明卻迷戀那種感覺。
白天時,她曾經偷偷上網查過。
在打出“乳”和“交”這兩個字時,她心跳的厲害,也臉紅的厲害。
網上說,這種行為隻會對男人有感覺,但對女方沒任何用處,算是增進夫妻感情的常見方式。
不過,并不是所有丈夫,都能享受到沈嶽今早享受過的那種感覺。
這就好比想品嘗酸的味道,最起碼得有醋,或者杏之類的東西吧?
任總有這個本錢,而且還是大本錢。
可讓她不明白的是,網上明明說女人在做這種事時,不會有任何的感覺,她卻覺得,比她的洞房花燭夜,還要更
任總覺得,那可能是她的心理做崇,是因為太刺激了,和不是丈夫之外的男人。
一整天,任明明滿腦子都在想這個問題,神魂不舍,總是出錯。
尤其在給老曹等人開晚會時,她明明是要問“各位,你們覺得,我們當前的訓練方式,還有哪兒需要改進的地方”,卻問:“各位,你們覺得,我給他搓時,要不要像網上說的那樣,搓點潤、滑油,來增加他的速度?”
然後,老曹等人頓時懵逼,面面相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這個問題問出口後,任明明隻感覺被炸雷劈了那樣,心髒狂跳。
全身的鮮皿,忽地都湧上了腦袋。
她連忙低頭,端起茶杯喝了口。
馬上她就劇烈咳嗽起來,左手捂着嘴,小臉漲紅。
看到任總喝水差點嗆死,可把老曹吓壞了,有心想過來給她捶捶背,卻又礙于男女有别,隻能不住的問不要緊吧,您小心點。
咳嗽了足足半分鐘後,任明明才止住。
差點嗆死的感覺,簡直不要太好,即算是懲罰任明明的恬不知恥,也算是掩飾她的臉紅了。
“我該怎麼辦?才能掩飾這要死的尴尬?”
就在任總假裝還要咳嗽,低着頭心中慌慌的想到這兒時,就聽老曹小心的說:“任總,您是問單杠上要搓潤、滑油嗎?”
任總雖說身手彪悍,更是警校高材生,但她終究不是安保訓練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那麼,她把在單杠上應該塗抹滑石粉,說成是潤、滑油,也很正常。
至于任總提到“搓”和“他”等字眼,老曹等人如果還想刨根問底,那就幹脆卷起被蓋回家就好。
别說是不能問,就是想,都不能想!
因為人們在想某些事時,就會從眼神内流露出來,就會被任總發現,就會卷起鋪蓋走人
為什麼要給那個“他”去“搓”,搓什麼等問題,很重要嗎?
和老曹等人的飯碗相比起來,可謂是輕如鴻毛。
老曹找了個還算合适的理由,可算是解了任明明的燃眉之急,立即用力點頭,故意皺起眉頭,若有所思的說:“我剛來打掃衛生時,曾經在單杠上做過幾個動作。當時沒用滑石粉,感覺掌心的皮膚,都快給搓破了。就琢磨着,用潤、滑油,應該更好些。轉動起來時的速度,也會更快。不過,用油太手滑,還要洗手。看來,還是用滑石粉更好些。”
老曹等人這才恍然大悟的樣子,連忙說任總所言極是。
好不容易把口誤彌補後,任明明真怕會再露出什麼破綻,很快就以天氣不早為借口,散會。
“以後,我再也不能胡思亂想了。要不然,早晚都會出事,被人們看不起。”
任明明回來春天花園小區,在車上呆坐很久後,才接連深呼吸,開門下車,擡頭看向了十樓。
主卧次卧還有客廳陽台窗口,都黑漆漆的。
看來,展小白還沒回來。
也許回來了,已經休息了。
但無論她有沒有回來,姓沈的那厮應該都走了。
想到沈嶽不再,得知展小白和她霸占這間屋子後,以後可能就不會來了後,任明明長長松了口氣。
隻要那個家夥不在,就沒誰能讓她心神激蕩,不用再犯那種錯誤。
可為什麼,任總剛松了口氣,心裡就空落落的,好像丢了多麼值錢的東西那樣?
患得患失中,任明明開門走進了十層西戶。
她知道客廳的開關壞了,所以開門後也沒去按開關,而是拿出手機随便照了下鞋架。
借着手機屏幕發出的光,任明明看到了一雙白色小高跟,就知道展小白已經回來了。
展小白既然已經回來,那麼任明明就不能再去主卧睡覺了。
雨停了後,天氣雖然很好,但終究不是夏天,被雨淋過的次卧,應該還不會太幹。
“大不了,就在沙發上湊合一個晚上。反正,明天老早就要去單位。哈欠,真累。”
打了個哈欠後,任明明換好鞋子,晃着手機快步走進了次卧。
關門,開燈。
一切正如她所想象的那樣,過了兩整天,被雨淋過的被褥等,還是有些潮乎乎。
下周才會供暖,不然早就蒸幹了。
為了避免弄出動靜,驚到展小白起來看,任明明抱着睡衣走出次卧去浴室洗澡時,故意哼着小曲。
主卧内沒亮燈,看來展小白知道是她回來了。
匆匆沖了個澡後,穿着睡衣的任明明,從衣櫃内找出一床被子,關上燈走出次卧,抹黑來到了沙發前。
看着黑暗中的沙發,任明明眼前又浮現出了不可描述的場面。
昨天早上,她曾經跪在這兒給那個誰那個啥來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昨天早上的行為,要比今早的行為更進一步,可當時任明明卻沒任何感覺。
就是單純的給他弄,不帶有任何的感情。
就算事後想起來,也隻是懊悔,明明姐貌似太特麼的不要臉罷了。
哪像今早在主卧内,用兩個美白粉給那家夥搓時,會有那種身心都在顫栗的快樂。
她的皿液,又開始緩緩的沸騰。
房間内,好像也平添了很多淫、靡的氣息。
這種錯覺,讓任明明突增出某種渴望
趕緊用力咬了下舌尖,暗罵:“任明明,你也是正經女子好吧?怎麼現在滿腦子都是那麼龌龊的想法,不怕變成淫、婦嗎?好了,乖,别亂想了。睡覺。明天起來後,這些可怕的念頭,就會消失不見了。”
用疼痛趕走那些龌龊想法後,任明明不敢再發呆,轉身抱着被子,坐了下來。
她想坐在沙發上後,再躺下,然後展開被子蒙住頭,想想工作上的煩心事。
可她坐下去後,卻沒坐在沙發上。
而是,坐在了一雙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