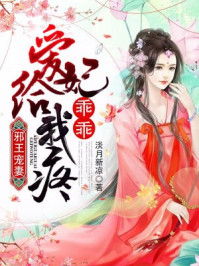就在湯媛離開的這段時日,京師并不平靜。
失去家族希望的甄閣老像瘋了一樣的撕咬章閣老,完全就是光腳不怕穿鞋的。
隻因他别無選擇,如今的賀纓除了一個嫡子身份再無優勢,可章閣老若是也也不幹淨,那一切就還有轉圜餘地。
其實明宗對這其中的微妙也并非一無所覺,然而俗話說得好,不聾不啞不做阿翁。手底下的人有貓膩當皇上的怎麼可能不清楚,可隻要不觸及底線,那也沒甚不好,總比抱成團兒的欺主來得強啊。
殊不知這樣的平衡在端午節的夜晚裂開了一條縫,那也是湯媛離開京師的第二日,當時章閣老正在家中昏迷不醒。
那日宮中當值的人乃甄閣老,明宗則在養心殿批折子,批到一半的時候忽然遣人宣甄閣老觐見。
沒過多久,滿臉凝重的甄閣老就邁入養心殿,一如當年他滿腹治國經綸第一次踏入文淵閣。
後來,甄閣老走了,明宗卻再無睡意,負手于殿中走來走去,神情亦是不同尋常的陰翳。
先帝生前共有兩子,一個是明宗賀陽,另一個幾乎已經被人淡忘,他就是先太子賀朝。
賀朝的生母乃先帝明媒正娶的詹氏,出生新貝府望族。詹氏自幼體弱多病,并不适合為後,無奈惠宗愛慕她至深,硬是将美人娶了回去。時過三年才得一子賀朝,将滿三歲就被立為太子,可見惠宗對他給予了多麼深厚的期待。
那麼當時的明宗在幹啥?他還在當今太後的肚子裡。太後也就是當年的範貴妃,豔冠後宮,卻始終敵不過藥罐子詹氏,可惜詹氏福薄,兒子一被立為太子就與世長辭。那時惠宗也沒有扶正範太後的意思,直到太子賀朝的身體越來越虛弱,種種迹象都表明這個孩子可能活不過二十,興許連子嗣都不會有,先帝這才放棄任性,開始關注明宗。
于是體弱多病的賀朝最終不得不因身體的緣故退位讓賢,之後受封忠王,還未開府就有了封号,也算先帝對他的一種補償。
世人都說明宗的成長之路無煩惱,殊不知忠王就是他一輩子的煩惱。
因為忠王成功的活過了二十,還順利的成親,最後那幾年居然又有了好轉的迹象,不過這種迹象于明宗而言不啻于滅頂之災。
那之後明宗有了第四子賀維,而忠王妃也生下了一個遺腹子,是個男嬰,據說那天先帝一夜未眠,捧着愛後詹氏的遺物流淚至天明。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先帝後悔了,他後悔立明宗為太子。
他就該再等等,等到那個男嬰降世,而他也正當盛年,完全有能力培養一個小太孫啊!
可是他卻沒有頂住宗人府的壓力,中途廢東宮,以至于父子隔閡多年。
由此,忠王留下的小世子也成了明宗心頭的一根刺。就是這個孩子,差點改寫了他一生。
這輩子他都忘不了先帝變幻莫測的眼神,數十次的欲言又止,但不管怎樣,最終他還是有驚無險的繼承了大統,事情到此本該也算有個了結。
卻萬萬沒想到父皇對忠王世子的愛竟遠遠的超過了對他的,更沒想到一直以來最為信任的兩朝元老章書廉就是那個上疏請封忠王世子的王八蛋!
此時明宗沉郁的目光重新落在書案,奏折泛黃,顯然有些年頭了,上面還有先帝的朱砂批閱。
他的父皇指使走狗章書廉上疏,以此試探滿朝文武口風,明宗深深地感到了一種被人背叛的疼痛與憤怒。
但更讓他背後發涼的是父皇竟還給最為信任的人留下了一道空白诏書。
這是什麼意思?
難不成還想憑這一道诏書掀了他的皇位,扶植忠王世子?
明宗怒極反笑,那也得扶植的起來啊!父皇若是泉下有知,怎麼不爬上來瞅瞅,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寄予厚望的是個什麼東西,腦子平庸,相貌也平庸,性格更是懦弱遲鈍,詹家就更不用說了,都還沒打壓已然蠢材輩出,讓這樣的人做皇帝,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恐怕大康也離亡國不遠了!
翌日,他禦駕親臨章閣老府,探視了這位位高權重忠心耿耿的好臣子。
甄閣老得意的恨不能在書房打個滾,卻也是不敢掉以輕心,畢竟世上沒有免費的餡餅,那個神秘人為何要幫他?
不止幫他還不曾提一句要求。
可惜神秘人從來不回答問題,甚至都不曾露面。
賀緘在飛螢館煮了一壺茶,泉水還未沸騰,珠簾外已經默默的出現了個人,那人嗓音沙啞,木然的禀明了甄閣老的小動作。
這樣真好。賀緘非常喜歡這群人像跳梁小醜一樣的互相揭短。
而章閣老做夢也不會想到當年那封迫于無奈呈上的奏折并未被銷毀,最後還落入徐子厚之手。
自古以來世家門閥除了積累聲望,也都酷愛積累旁人的軟肋,徐家自然也不例外,當年搜集了章閣老的奏折,可惜還沒等到發揮作用,自己就先被明宗給撸了。
不過奏折也非萬能,它必須出現在最完美的時機。何為最完美?自然是甄閣老放手一搏之際。
解決章閣老,再來一個延綏遇襲,此生便與前世完美的接軌,并且提前了一年。
賀緘抿了抿唇角,藏在袖中的手輕輕捏了捏粉色的碧玺小兔。
他并不敢明目張膽的去找媛媛,隻能派人小心翼翼跟在賀綸的人附近打探消息。
媛媛不會有事的。
他相信她會活着回來。
而他,一直都在努力為她鑄就一座金色的宮殿,隻為深藏她于其中。
京師的風雲變幻暫且不再詳述,隻說湯媛一行人在大同鎮稍作休整,等來了另外三名星宿,方才浩浩蕩蕩的重返京師。
原來平水關那日鬼宿被數名苗疆亂黨圍追堵截,方才遲來一步,也虧得她速度快,再遲一遲大家夥說不定就要被亂黨一網打盡了。
直至五月十九,消失了半個多月的湯媛終于推開了裕王府的角門,恍惚如隔世。
她激動的都不知該撲過去找幹爹還是撲過去找賀綸。
是了,還是先找賀綸吧,畢竟她有一大堆重要的話兒要跟他說,而幹爹說不定還在睡覺呢!
鬼宿都沒來得及提醒湯媛沐浴更衣,就見她就撇開自己的丫鬟飛奔朗月堂,肩膀擦過紛繁的紫色小花兒,撞開一陣馥郁的花雨,也吓得馮鑫老遠就開始避讓。
賀綸還是老樣子,坐在八角亭的石凳上品茶,每天晨曦他都會在這裡稍坐片刻。
目光瞥見湯媛也沒甚大波瀾,卻依舊深深的,望一眼就會淪陷的黝黑。
“阿蘊!”她很想他。當賀綸微微張開手,她就沒有猶豫的跳進他懷中,緊緊的環住他脖頸。
馮鑫恰好撞見這一幕,簡直是豈有此理,多大的人了,還是小孩子嗎,竟敢騎在王爺腿上!辣的人眼睛疼。他連忙轉過身。
賀綸安靜的抱了她一會,若非那雙手正輕輕的摩挲她因開心而亂晃的雙腿,她都要懷疑他是不是真的喜歡自己了。
“你怎麼不說話啊,看到我不高興嗎?”湯媛問。
賀綸深深看了她一會兒,才道,“臭臭的。”
嗯?湯媛噎了噎,一顆心霎時就要碎了。
死裡逃生!
時隔半個多月才相見!
聽到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臭臭的”!
呆怔了許久,湯媛的眼圈慢慢的就紅了,“你這個混蛋,既然臭當初幹嘛還對我表白……”
賀綸微微上前,吻住她,右手輕輕捏住她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