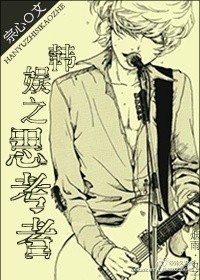太陽西斜,又開始刮風,先是地上的雪粒在慢慢滾動,緊接着就成了一條白色的雪龍,數千,數萬條雪龍彙集在一起,就成了漫天的白毛風,單雄趕緊找一個避風的地方,要不然他就會被白毛風凍成雪雕。
轉過山腳,他看見了一座閣樓,遠遠地就見周圍有幾個仆役打扮的人在走動,從他們的穿着打扮看,很像早上來請林凡前去赴宴的那些人,看到這些人,單雄暗暗驚喜,終于找到了林凡的蹤迹,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啊。
陣陣寒風吹來,還帶來斷斷續續的笑聲,單雄無法從這笑聲中辨别出是否有林凡的聲音,也無從判斷林凡是否還在裡面,但無論如何都要上前查看個究竟。
閣樓周圍的美景單雄不感興趣,至于閣樓是建在一輛奇怪的車上,他也隻是多看了兩眼便無視了,他的注意力在周圍那些走動巡邏的仆役身上,他的目光四處瞟動,時刻注意四周一步步向閣樓摸去。
正門單雄不敢走,所以他就摸向後方,這邊有小竹林遮掩相對安全些,閣樓是用巨大的車輪撐起來的,後方沒有樓梯,離地足有一丈。
單雄四處看看發現依然沒有人發現自己的蹤迹,于是就卸下革囊,縱身一躍,就攀住了平台,腰腹一用力,就上了閣樓,這時他聽清了裡面的聲音,依稀可聽見林凡的歡聲笑語,一顆擔心的心總算放下來了,可又有心不甘,人家擔心半死,你卻在這裡如此快活,不公平啊。
透過窗戶,他發現林凡很快樂,想想這一路的奔波,單雄氣不打一處來,用力一推窗戶,然後用手一用力,整個人就翻了進來。
對于單雄的突然闖入,除了林凡和二蛋像早已意料一樣沒有感到多麼驚訝外,其他人都面露驚容,公輸孝也就是之前帶林凡回來的那個青年男子,第一個站了起來,剛要咆哮,見是林凡那邊的人也就忍了下來沒發作。
“原來是林侯身邊的護衛,來,來,來,吃點東西暖暖身。”公輸孝陰沉的臉在認出單雄後變成了一張笑臉,笑吟吟的招待。
墨傳和公輸忠見公輸孝這般反應才知道來者,本來要叫人了,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也忙招呼起來,單雄一點都不客氣,坐在林凡身邊拿起酒壺自斟自酌的喝起來。
單雄能按計劃前來,林凡很高興,雖然局勢并非最初所設想的那樣糟糕,但能來說明他還是講義氣的,至少不會明知有危險就丢下林凡一人離去。
為了表達這份情,林凡給單雄又是斟酒又是夾菜,單雄似乎非常餓了,吃得歡快,也沒時間與林凡計較這一路上的奔波之苦。
林凡往外瞅了瞅,見天色漸黑,外面疾風爍爍,也就絕了回軍營的念頭,在這裡過一夜明日出發也好,有了過夜的念頭,他就更放心吃喝了,既然眼前這兩位大古世家要加入林氏學府,那就是自己人,沒必要再擔心安全上的問題。
好好吃了一頓,美美睡了一覺,第二天林凡才帶着二蛋和單雄一起離開了這裡,墨傳和公輸忠他們不願意與林凡一起走,他們可不想與大唐軍方打交道,雙方約定好在長安會面・・・・・・
大将及老兵等人見林凡平安歸來,一顆懸着的心總算安定下來,車隊繼續按照原計劃向陰山進發,一路上,二蛋依然處于亢奮狀态,與老兵說着昨日所見所聞,以及所享受的種種待遇,聽得老兵沒有什麼感覺,倒是使得其他府兵也亢奮起來,他們恨不得昨日與林凡一同前去的就是自己,這種待遇此生恐怕都享受不到。
十天後,林凡比預期提前了六七天抵達陰山,到了這裡,林凡隻是與薛仁貴、牛忠仁、蘇定方三人稍微寒暄幾句,就被李靖拉着去治療依然活着的傷員。
這次總有林凡忙的了,傷兵營足足占了整個營地的三分之一,傷員與十幾天前在白道聽信使所描述的相差無幾,人數依然是兩千來人,之前傷重的基本熬不過來走了一部分人,隻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大海從來就不缺水,傷兵營的空缺總是有人填上,起初隻是輕傷的将士在這種天寒地凍的天氣裡,逐漸都成了病重者,就好像後世都市的醫院一樣,空床的現象很少發生,你走總是有别人住進來。
這是一項大任務,林凡的府兵營開始真正的起作用了,林凡帶着自己的軍醫隊開始在傷兵營中穿梭,首要目标是重傷者,這些重傷者隻能林凡親自動手,二蛋雖然在他身邊學了一段時間,但也隻會做些簡單的手術,技術還不夠純熟,傷重者自然不能交給他。
傷兵營的重傷者高達五百多人,這可就累壞了林凡,經過一天一夜的不間斷手術後,他的任務終于完成了,這個過程讓他仿佛回到了後世那種工作的日子,這總算好些了,以前他兩天兩夜呆在手術室裡都呆過。
剩下一些輕傷的傷者林凡不打算親自動手,這些人給二蛋做練手的試驗品最好了,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怎能錯過。
不管這些人是否願意,林凡都做好了這個決定,二蛋得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隻是苦了那些傷員,他們擔心在二蛋的針下要受很大的苦。
林凡不放心讓二蛋單獨去做手術,二蛋如今還沒有獨立動手術的能力,他得在旁邊把關,這件事不急,重傷者都已治療好,剩下的這些輕傷者慢慢治療來得及。
在好好的睡一覺後,林凡就有點閑暇了,薛仁貴和牛忠仁立馬來找他談笑,他們無非就是想告訴林凡這一戰的過程如何,講述自己威猛的經曆。
在和平世界長大的林凡對于戰争從來就不感興趣,聽着那些皿淋淋的畫面隻有反感,可他阻止不了這些殺才的那一腔狂熱,他隻有當他們的話當耳邊風,這樣才好受些。
薛仁貴第一次參軍非常的興奮,這次經曆徹底将他骨子裡的殺才本質淋淋盡緻的展露出來,每說到殺敵的場景,他都手舞足蹈,說得唾沫橫飛,林凡沒有注意他所說那些戰争畫面,他在盯着薛仁貴那有些臃腫的手看,基于職業的本能,他想到了薛仁貴右手估計是得凍瘡了。
“讓我檢查下你的手。”
薛仁貴暫停了下來,伸出右手,滿不在乎地笑道:“不知為何早上起來就有些臃腫了,不過沒有什麼的,隻是腫了一點而已,過一兩天就好了,又不會疼。”
林凡笑呵呵道:“現在不疼,晚上會癢死你,就像幾百隻螞蟻在你肉裡撕咬,想想那滋味,真是可怕啊。”
“癢有什麼好怕的。”
薛仁貴拍拍兇膛信誓旦旦道:“千軍萬馬都熬過來了,還怕這一點點癢?”
林凡指着薛仁貴悠悠道:“話不能說得太早,晚上可别後悔啊。”
“是啊。”
牛忠仁拍拍薛仁貴的肩膀道:“這種癢永比殺敵難受多了,想當年我第一次往北方作戰時也遇到這種情況,當時也以為沒什麼,可到了晚上那個難受啊・・・啧啧,真不知該如何形容,不過啊,這是僅有的一次,因為你從未來過北方這麼寒冷之地,水土不符,等你适應了這種陰寒天氣也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你看看我,現在把手放在雪裡凍一個晚上也不會像你那樣腫得跟豬頭一樣。”
薛仁貴嗤之以鼻,揚着右手大聲道:“老子行軍這麼久都未出現過這種現象,如今剛松懈下來沒幾天就長出這麼一個玩意,怕啥啊,不怕,老子今晚倒是要瞧瞧這玩意究竟有多麼神奇之處。”
薛仁貴這麼固執,林凡也不好再多說什麼,搖搖頭也不想再給他治療,這小子沒給他一點苦頭吃就不知道‘難受’二字怎麼寫。
“那我們今晚就做個試驗怎麼樣?”
對于林凡的這個問題薛仁貴很奇怪,牛忠仁更奇怪也很好奇,張着那雙大眼傻傻地看着林凡,等他說下去。
林凡掃了兩人一眼,最終目光落在薛仁貴身上,臉上帶着壞壞的笑容:“今晚你睡覺時就把你的雙手綁在床上,看看你晚上能不能受得了這個癢。”
“好,誰怕誰!”
牛忠仁就不是什麼好鳥,聽到這個提議後連連拍手叫好,比林凡還期待夜晚的到來。
夜幕降臨時,薛仁貴被林凡早早地推到床上去,不用林凡多說什麼,牛忠仁很積極地就過來将薛仁貴的雙手綁得結結實實的,做完這些兩人就坐在薛仁貴的床前,看他的反應。
薛仁貴很淡定,悠然自得的談笑風聲,漸漸地,他的注意力不在談笑上,卻是往右手看去・・・果然就如林凡所言沒到半夜,薛仁貴的右手就瘙癢難忍。
剛開始他還為了面子強忍着,小心翼翼地讓右手在床闆上慢慢摩挲,這樣沒堅持半個時辰,他就受不了了,談笑根本就不可能了,在床上拍着床闆大叫,左手卻夠不着去撓,已經被牛忠仁綁得結實,掙脫不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