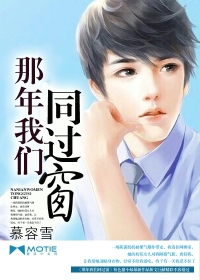“嗯!既然如此,那麼你便五天後出發!”
不知道什麼時候,荀靖突然間出現在了門口,沖着半側過身子去的韓言說了這麼一句。
“什麼情況?”
聽見門口那邊傳過來的聲音,韓言忍不住轉過了頭去。
隻不過等到韓言轉過頭去之後,荀靖已經邁步離開的房門口,倒是把韓言看得一愣。而在書桌旁邊的羊秘,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了韓言的身邊,與韓言一同呆呆地望着荀靖遠去。
“我說大秘秘啊,我老師這是……”看着自己的老師遠走,韓言很是無言,轉過身去就想跟羊秘說話,隻不過剛轉了一般就看見了湊在自己身側的羊秘,當即就吓了一跳,“怎麼……啊!大秘秘你什麼時候過來的!”
“你叫什麼叫?大驚小怪的,我這不是才過來嘛!”韓言一嗓子聲音可是不小,直把羊秘的耳朵給震得嗡嗡作響,連着掏了好幾下耳朵之後,這才開口抱怨起來,“我說你這一驚一乍的都是跟誰學的?要不是我膽子大,現在已經被你吓死了!”
緊跟在羊秘身邊的羊衜,這時候也跟着幫起腔來,“就是就是!你這咋咋呼呼的,一點都沒有個大人沉穩的樣子,還不如我呢!”
“嘁!我這叫率真本性,你們兩個懂個屁!”
韓言的臉皮可是在後世‘磨煉’過的,自然是不會在鬥嘴方面輸給身邊的這一對羊家的兄弟。
“你……”可能羊秘也知道要是論‘不要臉’的話是鬥不過韓言的,因此隻是瞪了韓言一眼,緊跟着就轉換了話題,“玄行先生剛才說的話你都聽見了,你打算怎麼辦?”
“怎麼辦?還能怎麼辦?回去休整一下,五天之後出發呗!”
伸出右手的小拇指扣了扣鼻子,緊跟着隐晦地往羊秘的身上彈了彈,韓言很是無所謂地說道。
“五天之後出發?你有什麼打算嗎?”
見韓言這幅無所謂的樣子,羊秘的心裡真的很是不踏實。
“打算?這不還有五天呢嘛!先去準備一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如果要是進展順利的話,咱們應該能趕上我兒子的滿月酒!”
仔細盤算了一下,韓言覺得時間上可能有一些趕了,隻不過也未必會差太多。
“你兒子的滿月酒?五天後出發,到青州的治所臨淄城就要十天,一來一回二十天,剩下五天的時間你能做些什麼?”
看着韓言那副無所謂的樣子,羊秘的心中就是一陣擔憂,忍不住跟韓言盤算了起來。
“五天的時間能做什麼?我告訴你,五天的時間我就能拿下臨淄城,你是信也不信?”
斜了一眼羊秘,韓言的臉色開始顯露出了一絲不屑。
“五天的時間拿下臨淄城?韓兄,你這話說得可是有些大了啊!”
雖然說羊秘算是半個書呆子一樣的人物,卻也知道現今青州的局勢是如何的困難,因此很是不相信韓言所說的話。
“哦?你是不信?既然你不信的話,那不如我們打個賭如何?如果五天之内我拿下了青州的臨淄城,你待如何?”
心中明白跟書呆子是說不清這些事情的,韓言幹脆就不去跟他解釋,而是打算跟其打賭了。
“兄長,不……”
後面的那個‘可’字還沒有出口,羊衜卻是再也沒有機會說出來了。
羊秘似乎是受到了韓言的刺激,臉色漲紅,喊叫起來,“好!既然韓兄你如此有把握,那隻要你在五天之内拿下了臨淄城,那以後我羊家便以你韓言馬首是瞻!但是,如果韓兄你想要是五天之内拿不下臨淄城,那又該如何?”
“五天之内拿不下臨淄城?那不可能!你就乖乖地等着當我的馬仔吧!”
韓言又不是傻子,自然不會下套把自己給套上,嘴一撇,邁步就離開了隻剩下兀自生氣的羊秘還有一臉無奈的羊衜留在了原地。
“唉!兄長,你可真是……可真是……”
看着自己的這位親大哥,羊衜簡直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了。
如果韓言要是做不到的話,賭約對他根本就沒有效力,因為人家根本就沒有下注!可是羊秘呢?羊秘要術輸了賭約,以後羊家還有什麼地位?自己的哥哥聰明一世,羊衜簡直不能相信自己身邊的這位竟然是自己崇拜了那麼久的親大哥。
“可真是什麼?愚不可及嗎?”
臉上的紅暈還未消散,但是羊秘的語氣卻是詭異的平靜了下來。
“啊?大哥你……”
感受着自己的大哥與方才迥異的态度,羊衜頓時就是一驚,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我?我怎麼了?”羊秘白了自己的弟弟一眼,沒有再多說羊衜什麼,反而自顧自地說了起來,“有些事情,身為一家之主考慮的自然要跟常人不一樣,這個賭約看起來對我們羊家很是不利,可是誰又能知道,這對我羊家才是最大的好處呢?”
“最大的好處?”
羊衜眨了眨眼,感覺自己完全理解不了自己的哥哥說了些什麼。
“沒錯,最大的好處!”肯定了羊衜的疑問之後,羊秘的聲音緊跟着低了下來,“如果韓有信能夠在五天之内拿下臨淄城,那麼我羊家就以他馬首是瞻又如何?現在的羊家需要的不就是一座靠山嗎?而如果他五天之内拿不下臨淄城,對我羊家又有什麼損害?衜兒,這家族的處事原則,你還有得學啊!”
“兄……長?!”
看着自己身邊的羊秘,羊衜第一次覺得是那麼的陌生,就好像自己身邊的這個人不是自己的兄長,而像是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一樣。
“好了!沒什麼事情我們就先回去,雖然說現在天下已經亂了請不來什麼人,但是總歸要給韓兄的兒子辦一場喜宴,如此,才顯得不失我羊家的臉面。”
神情一收,剛才那個面色冷冽的羊秘又變回了原來的模樣,很是輕松地說着。
羊衜站在一邊沒有說話,反而在不停地思索着自己兄長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