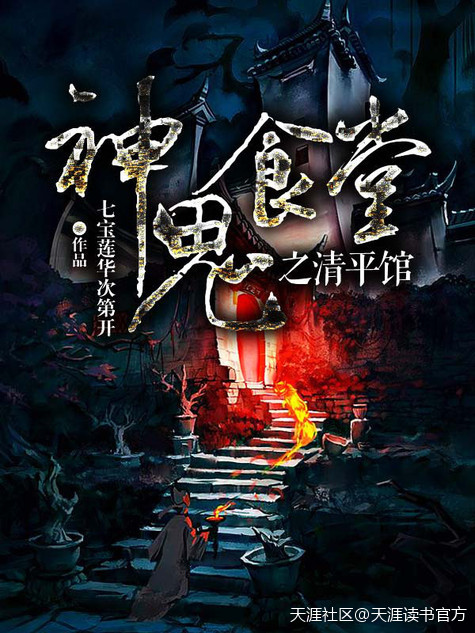豪宅,麗人,恍如仙境。
進了大宅,如進一坊,仍是車馬前行,曲曲折折,來到第五淩若處。
仆從如雲,接迎如儀,入得室中落坐,已有香茗侍候。第五淩若去換了一身燕居的常服,輕軟貼身,伴着李魚聊聊了今天的事情。從旁點撥了一番,這工程之中許多容易做财務手腳的關節處,李魚已是豁然開朗。有這麼一個理财專家一旁竭力提點,旁人想把
他當外行糊弄,已是不可能了。至于哪些環節如何省錢,甚至拆除舊靈台如何廢物利用,如何處置用不上的廢舊材料,以及從工部提來的款項如何在安全的方式下又能避免資金閑置,第五淩若都有提及,這位理财專家,可不僅僅有能監
督他人,避免貪污浪費的手段。
第五淩若見他用心記着,掩口笑道:“罷了,回頭兒借你一個賬房好了,有個自已人盯着,那就穩妥的多。”
李魚遲疑了一下,道:“這個……我任監造……卻大肆任用私人,這恐怕……”“一朝天子一朝天,為什麼?就因為非如此,不足以如臂使指。民間百姓,一聽這句話,似乎就覺得那些做臣的似乎受了委屈,其實呢?世上有幾個聖人大賢?人有六欲七情,便一定有私心私欲,區别隻在
于這私心私欲的大與小。
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尚且如此,才能政令通達,何況是你,上上下下,牽絆無數,不是什麼事都由得你作主的,可真若出了什麼纰漏,難道要皇太子去頂缸?必然要你背黑鍋的!”
第五淩若乜了李魚一眼,眸子貓兒一般的眯起:“别是……不想讓我的人插在你身邊吧?”
李魚白了她一眼,一本正經地道:“怎麼會呢,你的人都任我插了,插我身邊一個人算什麼,幾個人都無所謂啊。”
第五淩若非常驚訝,瞪大了眼睛:“你在我身邊插了人?什麼時候?我怎麼不知道?誰呀?”
李魚道:“你呀!”
第五淩若有些茫然:“我?我怎麼了?”
李魚悠然喝茶,不再理會。
第五淩若面冷心熱,文雅點說屬于内媚,俗氣點說屬于悶騷,雖說十年不涉于情,可是混迹在西市這個小江湖中,耳濡目染,也不知聽過見過多少事情,算是個理論上的老司機了。
再反複想想李魚這句話,突然面紅耳赤,撲到他身上,咬牙切齒道:“該死的,天還沒黑就開葷腔兒。”
李魚笑着躲閃道:“若是天黑了就可以開葷腔了是麼?”
兩人笑鬧一陣,第五淩若钗橫鬓亂,嬌喘細細,這才放開李魚,桃腮紅暈,風情萬種。
廳堂之上,就有四名俏婢侍立,第五淩若毫無顧忌,李魚也是入鄉随俗,早習慣了無視于她們的存在。實際上此時的大戶人家,夫妻敦倫,都常有叫侍婢一旁侍候,端茶遞水,逢迎清潔的。
本來如此私密之事,萬萬不可叫外人看見,否則男的還好些,那女子羞也羞死。隻是這内室侍婢,屬于一種很特别的存在,在時人觀念裡,并不把她們當成某種意義上的“人”。
李魚這才摸着鼻子道:“我隻是顧慮,施工匠作,全賴楊叔推介。而内政财務,又全賴你來扶持,似乎……顯得我很沒用。”第五淩若道:“糊塗。難道每一個可用之人,都得是你親自去一個個尋來?這樣的格局,頂多開個作坊,如何做得大事?你需要什麼,你身邊就有熟稔這方面一切的人,及時提供給你所需要的人和東西,那
就是你的本事。你做得到,旁人做不到,這不是你的本事是誰的?你你我我的,分那麼清。”
李魚握住她的柔荑,道:“怪我怪我。其實找楊叔幫忙時,我都沒有這許多顧慮。唯獨對你……那不同的……”
第五淩若凝眸望他許久,輕輕軟倒在他懷中,貼着他的兇膛,柔聲道:“我知道,男人,先天就比女人背負了更多,責任、榮譽、尊嚴,外面所有人對他的評評點點。但你對我,永遠不需要考慮那麼多……”第五淩若深情地望着李魚,輕輕地道:“我永遠都是那個在兵慌馬亂中失去了眼睛的那個小淩若,需要你的保護、需要你在我身邊,我才會覺得踏實、安全,你就是我在那一團黑暗中找到的光,是我的唯一
……”
你是電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話,我隻愛你youaremysuperstar,你主宰我崇拜,沒有更好的辦法……
不知怎地,李魚腦海中忽然冒出了這首歌,再一想到第五淩若長袖飄飄,霧寰雲鬓,手裡拿個麥克風,踏着歡快的舞步……李魚趕緊打消了這令人直冒雞皮疙瘩的想像。
第五淩若是絕不會想到,自已一番深情款款的表白,被一首歌給破壞了,偎依在李魚的懷中,想着過往種種,而良人就在眼前,從此長相厮守,再不用分開,她的心中無比甜蜜。
翌日,李魚趕到欽天監時,神采熠熠。第五淩若很懂得如何保養她的男人,在飲食上極盡細緻,想必是請教過藥膳名家的,飯菜色香味俱佳,營養又極好。昨日又已過了受孕期,兩人并肩共枕,隻是愛撫叙話,這一覺醒來,李魚隻覺自已精力
旺盛,挺一挺腰杆兒骨頭節兒都咔吧作響,又是一條生龍。
包繼業包先生比誰到的都早,他站在欽天監門口,大肚腆腆,笑臉迎人,見了進衙門的人,是官兒就鞠躬,是吏員就拱手,跟一隻杵在那兒的活體招财貓似的。李魚的車子一到,包繼業就跟舞台上的戲曲高手似的,一路行雲流水地過來,肩不搖,袍不動,雙腳在袍袂之下移動,仿佛滑行了過來,車子剛停穩,他的手已經穩穩地伸了出來,往那兒一架,充當了扶
手。
“李監造,您慢着,慢着……”
李魚腰杆兒一挺,跳了下去,沒用他扶,笑吟吟望他一眼道:“你倒來的早。”
包繼業點頭哈腰地道:“應該的,應該的。”
他往車上看了一眼,道:“楊大梁沒有同車來麼。”
李魚道:“楊大梁是個存不住事兒的人,這不,昨天與李秋官聊了一下,連夜就趕了工。早上起來,他還在睡,我沒叫他。反正建在拆之後,咱們先去安排一下拆靈台的事情。”
“好好好,一切聽您安排。”包繼業一邊說,一邊走,心裡盤算:“李魚這是明顯掌控着西市啊。第五大梁是我西市兩大财神之一,自從喬大梁死了,兩大财神兼而為一,都是她的,而她是李監造的女人,錢上,人家不差錢兒。我得探
探他的口風,胃口有多大,又或者他剛到工部,有心做一樁政績出來,瞅不上那點小錢。”“再一個,拆靈台還要商量?這李魚不是外行啊,裡邊的門道,看來他知道的不少,在這樣的人面前,我可不能耍小聰明。想抱人家的大腿,就得讓人家覺得我這人可信,可信才能可用。細水長流,不在這
一事一利上,我得規矩一些。”
李魚不曉得自已昨兒從第五淩若那裡了解了些東西,這随口一句話,人家這真正行家就據這細微線索做出了如許之多的分析。
兩人到了欽天監,尋到袁天罡的簽押房,又等了一陣,袁天罡才姗姗來遲。
見李魚已經到了,袁天罡對他辦事的态度倒是蠻欣賞,馬上把李淳風也喚了來,與他一商量,既然建造圖紙尚未出來,這兩位便興緻勃勃。隻涉及先拆的問題,就讓他們自行處理了。
李魚便帶着包繼業去了靈台。
這靈台如此龐大,所用建材可不隻是土石。因為涉及天文,内裡建構其實蠻複雜,看似一座台子,可裡邊卻是中空的,有諸般儀器的内部構架。
李魚一一指點,他也懂得藏拙,話隻說一半,省得叫人看出虛實。聽在包繼業耳中,卻是人家李監造果然是行家,倒也老老實實,不敢有什麼小算盤。不過聽到李魚要把一些小型儀器也充作鐵器銅器熔毀充作新儀器的原料,包繼業可忍不住了,小心翼翼地建議道:“李監造的籌劃,自然是最妥當的。小人隻是有個冒昧的想法,跟李監造提一提,小人思慮
沒有李監造那麼周詳,要是說的不對,您别見怪,要是……”
李魚實在忍不住了,道:“包先生隻管坦率說來,不用諸多顧慮。”
包繼業咳嗽一聲,幹笑道:“是!是這樣!其實對欽天監,民間多以為神聖之地,認為我欽天監諸官史,都是天上星宿下凡,所以知曉天上之事。而這諸般儀器,在百姓眼中,也都成了神聖法器。所以……”
李魚眨眨眼:“你是說?”
包繼業道:“把這些生了鏽的、蝕爛了的法器拿去民間,多的是大富豪紳不吝萬金購買啊,如果隻是融煉了充作五金原料,未免……太可惜了些。”
李魚一個“好”字差點兒脫口而出,不過話到嘴邊,卻是心頭一動,一下子又咽了回去。
這個年代,與自已所處的年代有許多不同。起碼在自已的年代,沒多少人把天文台氣象局視為如此神聖莊重的所在。這裡面有沒有什麼避忌,可不好說,還是先找行家問問才行。
所以,李魚不動聲色,淡淡點頭:“我知道了,這事兒我考慮考慮再說。你先四下勘察一下,确定拆除靈台所需用具、人數、時間等等,回頭把一應估計告訴我。”
包繼業答應一聲,便颠兒颠兒地去勘察靈台了。
此時,太子李承乾業已擺駕奔欽天監來了。
這件事對他的政治意義頗為重大,所以太子也極為上心。
而在太子車駕之上,本應隻有太子一人坐在車中,此刻他旁邊卻傍了一個人。彎眉秀目,膚色白皙,櫻桃小口,鼻如膩脂,秀美的比女人還像女人,正是太常寺樂童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