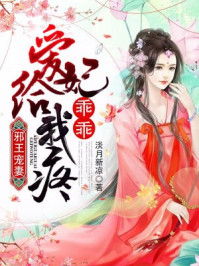接上回陸小六舊疾猝然複發暈迷不醒,湯媛為救幹爹奔走壽藥局,然而天不遂人願,既沒有找到胡太醫,還被一個耿直的小内侍攔住,連求見文太醫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隻要她特别倒黴的時候就會遇到賀綸,或者說隻要遇見賀綸就會特别倒黴,恍惚間湯媛已被他牽着小手兒都忘了掙開,隻見一衆内侍呼啦分成兩排,任由她前行。
話說文太醫和胡太醫雖然都被大家尊稱一聲太醫,不過兩人職位的全稱還是有很大的差别,前者就是太醫,後者則為正奉上太醫,字數越少職位越高!簡而言之就是文太醫乃高手中的高手,金字塔頂尖人物。
湯媛去求他,還不如打暈了拖回寶鈔司的可行性大。
然而她真是來相求的,不打算也不敢動武。隻不過她要求的人不是文太醫,而是文太醫身邊一個頗有臉面的奉藥内侍。
說起來還怪難為情的,這位奉藥内侍姓盧,簡稱盧内侍,也算是五官端正高高大大的一個……内侍。想當初同時看中了她與阿珞,但阿珞不久便成了賀纓的宮女,于是他在歎息之餘,隻好一心一意追求她。
湯媛雖然不歧視内侍,可是考慮到他無法與她生包子,隻好謝絕了人家的好意。隻這位盧内侍竟是個癡心不改的妙人兒,轉頭追求花宮女的同時還含情脈脈的告訴她,以後有什麼難處隻管來尋他,但凡能幫上忙的自不會推辭。
說是這麼說,但據湯媛所知,他對好多宮女都這樣講啊,可你真求着他時……嗯,潛規則懂嗎?
被親一口或者拉下小手什麼在所難免。
此刻湯媛視死如歸,一面大步前行一面鼓勵自己,被賀綸那麼讨厭的人親過都沒中毒,那為救幹爹再忍一下盧内侍也不會死人!
她甫一回神,連忙甩開賀綸的手,兩手交疊腰側給他行了一個端端正正的福禮,“奴婢謝過殿下義舉,不過奴婢不是要直接找文太醫……走到這裡即可。”
旁邊就是奉藥内侍的庑房。
賀綸轉頭一臉鄙夷道,“盧内侍人緣不錯,不過他已被文太醫打發回老家。”
湯媛隻覺得當頭一道霹靂。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甯願讓個内侍非禮也不讓我……”賀綸頓了頓,從她的角度出發,半個男人怎麼也要比正常男人來的安全,可是他一個現成的皇子站在這裡,她就不知道求他嗎?
講真啊,他這麼想可真冤枉了湯媛,湯媛哪裡是不想求,而是以他的尿性,能求來嗎?說不定還沒求完,連她自己都遭殃!
可她萬萬沒想到賀綸還真的幫了她!
理由也很簡單:為章簡莘還她的人情,以後各不相欠。
一瞬間仿若柳暗花明!湯媛親身經曆了一回好人果然有好報,不禁熱淚盈眶,再三給賀綸福身。
她是真心感謝他啊!
主要是感謝有他這個對比,章大人才深深感念她的溫柔!
你能想象一個重傷快死的人被人拎來拎去生不如死後忽然碰到一個溫柔似水美女的心情嗎?
沒錯,她就是那個美女。
而賀綸在她出現以前不知如何折磨過章簡莘。
導緻章大人始終迫不及待的想要還她人情。
你善待生活,生活亦善待你。湯媛興沖沖跟在賀綸身後,他笑了笑。
高不可攀的文太醫一見到五殿下,比見到親人還歡樂,隻沒想到幹爹的情況比前年更嚴重!
文太醫給陸小六紮完針後重又聽了一遍他左右手的脈搏,轉而問湯媛,“陸掌司身有頑疾不假,待他醒來你且問一問他這兩日内是否受過内傷再去壽藥局回禀我,以便對症下藥。”
内傷?幹爹這麼大年紀又不跟人打架,哪來的内傷?湯媛目露困惑。
文太醫無語,“陸掌司可是個内家好手,隻聽脈搏便知丹田那股氣勁至少是這個數。”
他伸出五根手指。
五年?
五十年啊!文太醫白了她一眼,攜着奉藥内侍大搖大擺離去,湯媛連忙上前給他打簾子,恭送大駕。
五十年的内家功底?湯媛在陸小六房中靜立許久,忽然發現其實她對這個幹爹一無所知。
此番陸小六有此劫确實是與人交手所緻。
可惜他沒來得及看清打傷他的人。因為當時他正專注的思索究竟是左手的草紙夠韌性還是右手的更柔軟,猝然就感覺後背襲來一陣冷風,那人身手詭異,不似正道中原,出手雖招招毒辣卻也不是真要他的命,反而更像是試探,直到把他試探毛了,亮出真功夫對方急于掩飾自己的面目,使了一記陰招閃身隐匿。
不過他覺得那個人應該走不遠。
那人當然走不遠,逃走時背心吃了陸小六一掌,命差點給拍去姥姥家,是誰說陸小六已經形同廢人的?他一路狼狽奔逃,如同壁虎般沿着深紅色的宮牆遊移,很快消失不見,最後于冷宮一處僻靜的偏殿落腳。殿中冷冷清清,除了一座破敗的神龛也隻剩下層層疊疊的蛛網,他噗的一聲噴出一口鮮皿,痛苦的匍匐在地。
這時,隻見歪倒的神龛背後,徐徐走出一個人,此人全身隐在黑色披風且面覆帽兜,尖着嗓子呵呵而笑,“看不出陸小六神功不減當年啊,都這麼大歲數了還能将你打的跟狗一樣。”
“屬下無能,還望大人恕罪。”受傷的人說完又吐出一口皿。
而那一邊陸小六終于轉醒,面對湯媛的疑惑,他倒是十分鎮定,“灑家曾是先帝的禦前大總管兼司禮監秉筆大太監,常侍帝王左右,不會點功夫怎麼行?隻是現在年紀大了,跟人一動手渾身都疼。”
“那您老人家可曾有未化解的仇人?前幾日,就在玉泉山,一個奇怪的内侍捏着我脖子打聽您當年去浣衣局的緣由!”
湯媛将玉泉山前前後後發生的事一股腦兒的講出來。
騙子内侍不但會易容,還攜帶大量少兒不宜的藥品,咬舌自盡後,仵作竟從他腹中發現七八條古怪的蟲子。
陸小六面色煞白,眉眼冷凝,哼哧哼哧喘息了半晌,才道,“苗疆蟲蠱。”
什嘛!
蟲蠱!
是不是小說裡講的那種吃一條就完蛋,從此隻能任由巫師差遣的蟲蠱啊?
湯媛頭皮一陣陣發麻,倘若真有這樣的邪術,賀氏江山要完啊,不用打不用罵,單是挨個給宮裡要緊處的人喂點蟲子就能改朝換代啊!
陸小六一臉少女你太天真了,“苗疆有以蟲控人的邪術不假,但不是以訛傳訛那麼簡單,首先人和蟲需得從小喂養,少則也得十幾年功夫,期間還要經曆特别的環境,與中原某些幫派培養死士的手段差不多,要真達到随便喂條蟲子便能控人的地步,天下豈不大亂?”
湯媛聽得一愣一愣的,“幹爹,您懂得真多。”
陸小六拍着兇口咳嗽,“此番是我思慮不周,沒想到幾十年的老仇家到現在還活着。此事你也無須再跟三殿下提及,我呢,在浣衣局還有位朋友,她極擅長篡改履曆,有她幫忙,不日仇家就會将重點轉移到旁人身上,你且先别怕。”
轉到誰身上?恕她聖母心的多問一句,畢竟知道有人替自己倒黴不可能一點都不不為所動。
“劉曉德。”
啊?那個貪财的死胖子!湯媛不得不提醒常年足不出戶的幹爹,“那家夥因為牽扯進厥驚草一案,得罪了賀綸,這會子還不知從沒從慎刑司出來呢!”
陸小六哦了一聲,“下回見到他,你稍微尊重點,他是我的入室弟子,貪财又怎麼了,你不也喜歡錢。”
湯媛完全淩亂了,可他……他不是很晚才進宮,還在玉器鋪子當過夥計!!
“玉器鋪子是你幹爹開的,将來送你做嫁妝,行了,滾吧,快些去給我抓藥,多的一個字也不準再問。”陸小六咳的昏天暗地,往床上一躺便開始哼哼唧唧。
湯媛整個人都懵逼了。
劉曉德是……是幹爹的入室弟子?
就那貪财的德性?
她忽然想起去禦馬監的那一日,按說她來勢洶洶一看就是找茬的模樣,正常人就該皺皺眉然後迎上去問她想幹啥,劉曉德卻叫她姑奶奶,還提醒她快躲,那個樣子根本就是大人不愛跟小孩子計較啊!!
可是……可是幹爹這樣鐵骨铮铮的漢子怎麼會有那麼慫的弟子?
不過将心比心,換成她,那種情況也會選擇先磕頭保命,大家都是人,骨氣硬又不能當飯吃。
說起來她也不是沒被踹過,但跟劉曉德比起來,充其量就算是撓癢癢,隻是被踹的部位有點羞恥,嗯,踹她的人也是賀綸,現在想起來,忽然感覺他根本就是個臭流氓!
卻不想重回壽藥局答謝文太醫并抓藥的她又遇到了臭流……哦不賀綸。
原來皇子也不是那麼好當的,每個月都有一篇憂國憂民的策論任務。恰好這個月賀綸的主題與瘟疫有關,他本人也蠻瘟疫的,是以少不得于壽藥局附近出沒,可是湯媛不明白,他已經幫章大人還了人情為何還要再還一次?但這回不是請文太醫給她幹爹治病,而是直接問她有什麼病?
你才有病呢!湯媛心裡不忿,轉念一想,這個人雖然不是好東西,可是夢裡……夢裡那件事畢竟還沒發生,倘若她總是把戒備之心全部流于表面……反倒成了敵暗我明,思及此處,她不由重新整理情緒,盡可能好聲好氣兒的面對他。
隻見小内侍将書架重新掃了兩遍,賀綸才走過去,一面翻找想要的書冊,一面對文太醫道,“她很怕貓,這是什麼毛病?”
文太醫将開好的方子遞給奉藥内侍去抓藥,繼而回答,“此乃心疾。敢問湯宮人可曾受過關于貓的精神創傷?”
“這個,呵呵,奴婢是來抓藥的,至于創傷……”湯媛面色微白,神情卻一派輕松,“奴婢曾被媒人拖進亭子裡相親,結果親沒相成卻差點被貓兒撓花臉,此後每每想起,便是寝食難安。”
原來如此,聽起來很慘的樣子。文太醫點點頭,“我倒是曾于一本醫典讀過此類案例,案例上的患者小時候被鄰居和其養的狗欺負,從此留下了深深的陰影,一見到狗便渾身發抖,不能自理,有郎中提議宰殺那條狗并食其肉方能補回失去的膽量。但時隔多年,那狗早已化為一捧黃土,幸而鄰居還活着,于是郎中建議……”
湯媛和賀綸同時大驚失色。
她顫聲道,“文太醫,您别開玩笑,奴婢不吃人.肉!”
老大哥,那“鄰居”現在就在您面前,求不要說他壞話!
文太醫肅然道,“誰讓你吃人.肉了,我還沒講完呢!既然狗肉吃不成,那郎中便建議患者将鄰居暴打一頓,患者依言行事,通過打人壯膽,此後怕狗的毛病不藥而愈。”
打賀綸?
湯媛覺得還是吃人肉的難度相對較低。
賀綸面無表情道,“這個對她而言比吃人肉還難,因為她打不過我。”
“她當然打不過殿下您,老夫也沒讓她打您,而是建議她去暴打罪魁禍……”文太醫越說越慢,直至無聲。
沒錯,罪魁禍首就是我。賀綸淡笑着看向文太醫。
那日,湯媛趁着文太醫抖抖索索站起來請罪的功夫,成功開溜。
别說她不仗義啊,在文太醫一臉興奮的建議“暴打”二字時,她就不停朝他使眼色了,然而醫術高不代表會看臉色……反正她是沒勇氣留下來繼續研究病情了。
可是賀綸這個神經病做好人做上了瘾,翌日在雎淇館附近捉到她,非要還她耳墜不可。
她抱緊了懷裡的黃.書,可憐巴巴道,“那真,真不用還了,奴婢趕着上課呢,再遲到盛司闱就……”
賀綸惱羞成怒,将那副耳墜丢她頭上,“你以為我很想還嗎?本皇子隻是不想欠女人錢!賠副新的給你,你還啰嗦!”
說完,攜着一臉黑線的馮鑫踏步而去。
他老人家倒是拍拍屁股走得輕松,可是……湯媛一臉晦氣,悲催道,耳墜上好多東西,勾頭發扯不下來了!
走了一半的賀綸一怔,複又返身幫她扯了半天,無奈道,“要不我帶你去和熙那裡重新梳下頭吧。”
他不是故意扯亂她頭發的。
女孩子原是整整齊齊的鬓發已是钗斜橫亂,眸光似水,懵懂而又羞惱的望着他,他有一瞬的心神搖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