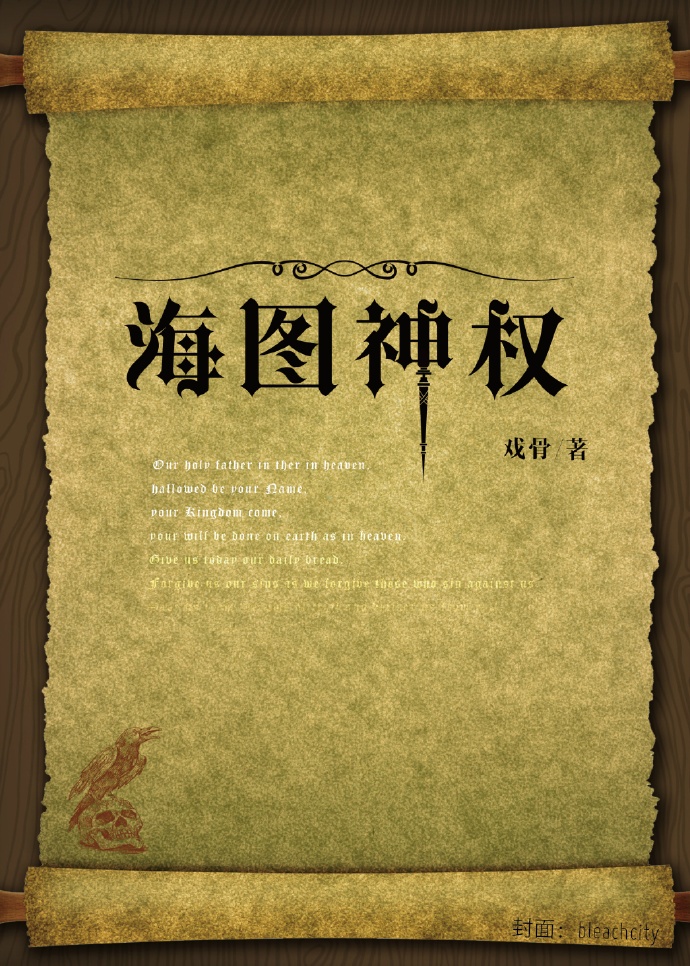賀雲昭回了家之後,便和程懷仁各自回院子裡。
程懷仁奔波了一天,也乏累了,在屋裡脫了衣裳,把當票收在枕頭下,沐浴過後,便傳了飯。
沈玉憐遮擋着半張臉,從後院到了前院來。
程懷仁剛吃過一半,聽說沈玉憐來了便把筷子停下,讓人去傳。
沈玉憐側着臉進來,與程懷仁見了個禮,便道:“表哥……憐兒來向你道歉的。”
程懷仁擺擺手,讓丫鬟和小厮都出去了,冷冷道:“沒什麼好道歉的,你好生看顧姨娘,讓她不要再鬧事了。”
絞着帕子,沈玉憐不安地想着,表哥果然還是對姨娘心灰意冷了。但這件事不是她鬧起來的,所以她要趕緊扭轉一下局勢,抓住程懷仁的心。
走到程懷仁身邊,沈玉憐捏着他的肩膀道:“表哥,我已經好些天沒見着你了。”
“不是昨兒在修齊院才見過嗎?”程懷仁瞥了一眼肩上的那隻手,又短又胖,不像嫡母的那雙手,纖細如一把水靈靈的青蔥。
二者相比起來,高下立見。程懷仁又把二人的身段樣貌放在一起比了比,賀雲昭比沈玉憐高了大半個頭,纖秾合度,氣度都比表妹不知高了多少層。
算了,根本就沒得比。程懷仁覺着自己簡直是無聊,居然拿沈玉憐和嫡母比,表妹是哪一點比得上母親的?!
沈玉憐被程懷仁刺的說不出話來,昨日那也能叫相見?那般場景,還不如不見!要早知是去受辱的,她昨兒就真的躲在院子裡,等事兒鬧完再去讨巧好了。
縱使程懷仁這般冷淡對待,沈玉憐也仍舊記得沈蘭芝的話,姑姑說了,表哥對她們最是心軟,他一向吃軟不吃硬的。
沈玉憐繼續軟着性子,柔聲道:“不過匆匆見得一面,我以前都是和表哥日日相見的,還記得咱們小時候一起在院子裡捉蝴蝶撈魚的時候嗎……”那時候伯府裡兩個嫡出的哥兒壓根不搭理程懷仁,都是沈玉憐陪着他玩。以前程懷仁在伯府地位很低,沈玉憐身份自然不高,和丫鬟沒有太大區别,隻是不用伺候人罷了。兩人從前也算同病相憐,關系才
那般親近。
如今卻不同了,沈玉憐依舊沒什麼地位,程懷仁卻已經是伯府裡半個主人了。而且在他心裡,表妹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珍貴了。
程懷仁聽着沈玉憐說的話,若是換做以前,他興許會心軟,心動,但現在,他的心已經漸漸硬了起來。他也能看得出來,表妹是故意在讨好自己,和小時候相依相靠的純粹感情,終究是不一樣的。
語氣淡淡,程懷仁頭也不擡,道:“天要黑了,你快回去吧。”
這是在趕她走了,沈玉憐咬着唇靜默了半晌,方道:“那表哥夜裡還去不去看姑姑?”她這是想幹那事,用身子來挽回他。
程懷仁不知為何,有些厭惡起沈玉憐來,一把揮開她放在他肩頭的手,騰地站起來道:“我要去書房溫書了,明兒還要去請先生,今兒要早些歇息,你快回去吧,孤男寡女省得下人說閑話。”
沈玉憐含着淚,低着頭沒有說話,她這般放低身段了,程懷仁居然這樣子對待她。薄情的漢子!她把最寶貴的東西都給了他啊!
程懷仁不想再和沈玉憐糾纏,便先一步打開門,去了書房。
沈玉憐呆呆地站了一會兒,轉身去梢間裡翻東西。沒了人,也總要得些财物。月錢不是發了嗎?錢肯定是從程懷仁這兒拿的,說不定還存着一些呢。翻找了一會兒,沈玉憐在程懷仁枕頭底下找到了當票,她死死地捏皺了當票,心裡改了主意……拿錢容易被發現,而且花不出去,捉到了就是偷盜。不如拿着當票,找不到這張紙,程懷仁與賀雲昭都不會痛
快!
沈玉憐藏好了當票,便從勤時院出去了,她心裡升起一股難以名狀的情緒,說不清是快意還是緊張恐懼居多。
偷當票的這一日,沈玉憐整夜都沒睡着,一直心驚膽戰地生怕被發現,擔心之餘,還是打算把當票給燒了!
……
程懷仁實在是被沈蘭芝氣壞了,心裡又惦記着請先生的事,睡了一夜都未發現當票丢了。大清早便起來,和明榮一起帶着薄禮,去了曹家族學,先拜别了原先的先生,再去的京郊見汪舉人。
一份厚禮,幾百兩聘師的銀子,而且還是學生親自來請的,汪舉人豈有不答應的道理?收下銀子,第二日就收拾好了東西到了忠信伯府。
汪舉人先去見過了賀雲昭,二人略交談了一番,相互客氣了幾句,他便正式開始給程懷仁上課了。
因着賀雲昭說過,旁的不論,隻要程懷仁能學好,這錢才不算白交。汪舉人把之前嚴待學生的本事加倍地拿出來,隻一天下來,程懷仁便累得夜裡倒頭大睡,話也不想說。
直到第三日,當出去的鋪子找到了買家,需要程懷仁拿當票和買家一起兌了地契過來,再去衙門裡蓋官印的時候,他才發現當票不見了!
三千兩可不是小事,程懷仁同汪舉人知會了一聲,先生也知道事有輕重緩急,便答應讓他先去辦事。
程懷仁頭一個念頭,就是去找賀雲昭。賀雲昭沒想到還有這麼個意外,她心裡根本不急這事,了不起再讓程懷仁兌一間鋪子去就是了,反正心疼的總不是他。因是冷靜道:“頭一個你好生想想,是什麼時候不見的。第二個想想有沒有生人進你的
屋子。第三個确認下是隻有當票丢了,還是平日裡也丢了其他小件不曾?若是常丢,隻怕是身邊的人手腳不幹淨,要是從未丢過,那就是别有所圖了。”程懷仁閉着眼好皺眉回憶道:“好像去請先生的前一天,就沒看見了,但兒子又累又忙,一會子沒往心裡去,至少是在請先生前一天之後丢的。要說生人,也隻有汪先生是唯一的生人,旁的人再也沒有了。
至于平日裡,我院裡的人我信得過,偷東西還是不敢的,您送來的兩個丫頭都很老實,也很少沒進過主屋,不是她們倆。”賀雲昭又分析道:“當票不比銀子,可以直接花出去。這玩意偷了,要是沒有銀子,也兌不到地契。若是能兌到,也要有三千兩才行,府裡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能一口氣拿得出三千兩白銀。我猜着,不是
為了銀子的緣故,約莫是别的意思——你近來是不是打罵了哪個下人?叫下面的小子記恨上了?”
睜開眼搖搖頭,程懷仁道:“沒有,近日來我同下面的小子話都沒有多說過,何談打罵,要真說記恨……”猛然瞪大了眼睛,他握緊了拳頭,想起了沈玉憐來找他的那日。
程懷仁不敢相信,自己青梅竹馬的表妹,會偷他這麼重要的東西?!但凡坐實了偷盜的罪名,那是要下獄的!
賀雲昭看着程懷仁變化不定的表情,道:“可是想到什麼人了?隻要有個懷疑,把丫鬟小子叫來挨個詢問排查就是,院子就那麼大,又沒有外人進來,除非他毀掉了當票,總能查出來的。”
程懷仁慘白着臉道:“兒子興許記錯了……可能不是放在枕頭下,是櫃子裡,兒子再去找找。”賀雲昭看着轉身就走了程懷仁,滿腹疑慮,這麼重要的東西丢了,他不把屋裡翻遍才怪,會找漏了地方?沖身旁的文蘭吩咐了一聲,讓她跟了出去,看看少爺到底去了哪兒,都查問了些什麼人。